设计为框架

Zaha Hadid 设计的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钢结构部分已构建完成,在新华网可以看到一些照片,大兴国际机场的设计是熟悉的 Zaha Hadid 的形态设计,大众会跟一些形象化的联想比如海星之类对其作出评价,作为一个大型的地标性公共建筑的必经之路,何况是像 Zaha Hadid 这类有机类的形态,首当其冲就是几何形态,大众不会去过问形态之外的内容。
项目内部的合理性必然是得到保证的,参与设计的有 ADPI 这样的机场设计公司,加上层层的工程验证,奇观式的外在几何形态之下具有合理性的支撑。
但是我们仍然会生发一些疑问,或许 Zaha Hadid 和 ADPI 一开始就介入了各种理性的因素,比如缩短入口和登机口的距离等等,而我们仍然对这种几何形态生成的设计师主观化成因深信不疑,对其形成的任意性充满怀疑。我们会去质疑设计中的合理性程度,是否这样的设计是最佳的方式?诸如流线型的形态、开放的视野和空旷的空间,是否对人员流动及指示有帮助,还是合理性迁就于视觉效果?设计师主观化表达为起始点,理性的因素不断介入去合理化,也包括对设计的阐述,我们对这一类的设计的质疑将会越来越多,源自科技的发展,以及设计工具的落后。试想,我们已经拥有足够巨大的数据支撑和强大的计算能力,去获取机场设计的最佳的合理性结果,是否仍有必要以设计师的主观表达作为起始?
我们面对的现状是:配备了一台高性能计算机但是只用来玩单机纸牌游戏。如今我们具有强大的计算能力和数据积累,但是计算机辅助设计,即 CAD,通常只是绘图,除了 CAD 还有 CAE、CAM 以及 PLM 等,但是归根结底,在设计端,我们仍只是用这时代强大的计算能力和数据资源来绘制几何形态。
比如像面对机场这样的工程,作为一个地标来说它的几何形态的形象含义还存在一定的讨论价值,但相比于其他内容,几何仅仅是一小角。我们能够意识到,对机场的设计来说,有太多的数据资源可以挖掘,有很多的可能性可以借用强大的计算能力来研究,为什么我们就只从一个设计师对几何形态的主观追求开始呢?如果我们有足够多的理性因素,我们仍会在于几何形态吗?
当然,对工具的研发和数据资源的整理也需要一个过程,我们现在还只能通过网络来很笨拙的搜索一些资料,比如在 Google 的图片搜索中输入某个词语,出来的东西仍是非常初级,我们仍然无法让计算机来自主建模,无法来遍历一些造型变种的计算。但是一想到我们有如此多的潜在资源可供利用,但现在只能用来玩纸牌游戏,就会心生困惑和焦急。
那么我们假设一下,如果这些计算能力的应用和数据资源的挖掘都实现了,设计出的机场会是怎样?包含更多的理性这是不用质疑的,但这种理性的综合表现会比当前的设计高多少?这是很难去想象的,或许高不了多少,或许那些主要的理性表现在当前的工作模式下已经覆盖到了。

或许更糟糕的是,这种对计算能力的应用和数据资源的挖掘,来实现的设计如果变成马岩松的金鱼缸式的设计,就会得到一个倒退的结果了。比如针对机场的交通和人员流动我们有很多的数据资源挖掘,然后我们遵照挖掘出的理性,得出的设计会不会是给人们挖出了一条固定的通道?如果一个东西的设计,它的理性层级是有限的,可以被设计师的思考所触及和覆盖到,是否有必要样样东西都要借助于大数据?
我们当前的设计手段包括思维和方法落后于技术的发展,否则我也不会仅仅使用计算机来辅助几何形态的设计,但我们无法去比较这两种方式那种更可靠,一是以设计师的主观创造为出发点再不断介入理性的修正,二是靠足够多的理性输入和计算能力为出发点辅助以设计师的修正介入。当一个设计的复杂度较高需要借助于计算时显然靠设计师是无法达到的,然而机器的理性和程序化却又是无法去讨论设计的符号意义的,也就是说有机形态的视觉效果、Zaha Hadid 的名声或者是来自于人而非机器的设计,仍然具有重大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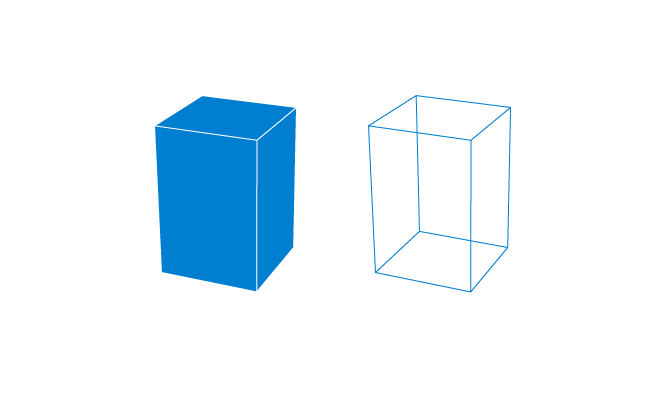
有两种形式的设计,一种是静态的,固定化的,实体的,一旦完成它就是定型了,需要外界来适应它,如果出现冲突,作出调整的是外界。一种是动态的,可变动的,框架式的,它没有完全定型,外界能适应它,它也可以为外界作出自我调整。
人是最具适应性的,所以当我们所处的环境没有太多活动元素参与时,一个静态的设计已经足够应付了,但随着科技和时代的发展,我们所处的环境越来越动态化,必然对自身的可调整型提出更高的要求,要求设计更加框架化。
让·皮亚杰(Jean Piaget)将人的认知过程中的适应行为分成两类,同化(assimilation)和调适(accommodation),即我们的内在世界已经具有一个认知模型,当与外界世界相接触时,同化就是将外界纳入已有的认知模型,无需对内在的认知模型作出调整,同化过程潜在的代价付出就是在对外界认知过程中会对其进行压榨,为了能够对号入座;而调适则是需要对自我认知模型作出调整或升级,因为外界无法纳入现有的模型之中,相对于同化,调适可能需要付出更多努力。皮亚杰认为这两类认知的形式是共存的,一个硬币的两面。
一个动态的可变的框架式设计,它也应具有很高的容纳性和能作自我调整的自由度。

Pentagram 为 Poetry Foundation 作的品牌识别设计,Poetry Foundation 是出版诗歌杂志《Poetry》为主,为将诗歌带给更广的人群,他们现在业务扩展到多个领域,比如活动组织和数字出版等等等。基于诗歌的一些特性,比如它特有的视觉形式——文字的排布——作为新品牌设计的起始点,将 POETRY 六个字母以 2 x 3 的分割排列,以这种排布的结构作为识别的基础平台,在此基础上可以容纳各种各样的变化(比如杂志的封面),而且识别性并没有得到稀释。
这只是“设计为框架”的一个机械式的例子。
科技的发展将很快会作用到设计这个行为上,计算机辅助设计远非只是辅助绘制几何形态,工具还未完备之时意识要先行,让设计从静态固定的实体化设计转向动态可变的框架化上。






